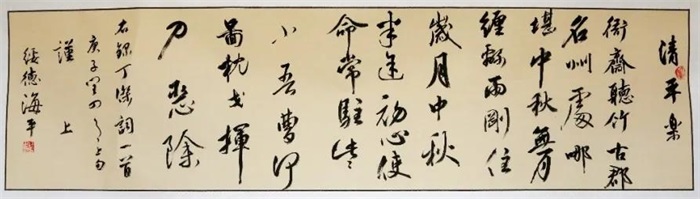拿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立在岸边的人,我奔着迟子建而来,奔着一个中年女人巧稚的思想和妙语而来,因为听闻的部分,远远比不得触摸的部分。当我进入《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阅读,我觉得一条河它动了起来,这动起来的河,那么沉又那么轻,它银波泛泛,它星光点点,它抛出的银带,将无数静立岸边的袍子,扎成了鼓风而追的骏马。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我是一个潮湿的人,一个记忆扇不动翅膀的人,一个被史诗般的言说渗透和浸润的人。我迷恋作者铺开的长链及长链上洞开的门和窗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和自己的三种关系,托起了小说一经转动就无法停歇的齿轮。它率先带领我进入那些一开篇就扑面的沧桑,带领我看到被褥上坐靠的迟暮老人,她的苍凉是时间玫瑰的瞬间绽放,她的倾吐是九旬之高关乎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建设和吹奏。那最后的子弹里,有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全力释放的火焰和焰火,有一支数百年前与贝加尔湖休憩与共、与驯鹿游猎相依为命共生共死的鄂温克人。这群人,他们身上背着瘟疫的侵害、猛兽的夹击,这群人,他们顶着日寇的铁蹄、也拖着现代文明的绳索。在迟子建的笔下,这群人蜿蜒而至,浩荡而至,他们有过流离、有过颠沛,但一条河,一条名曰额尔古纳的河始终成为贯穿他们身体和血液的内环,充盈起他们生活和精神丰厚的生态意蕴。这意蕴里,有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敬畏,有对生灵的护佑和关切,有对自然天性的礼赞和颂扬,更有对宇宙生态平衡秩序的思考和展望。她的小说里有宏大的叙事,但这些宏大是用一根根银针和黎簇搭建而就的楼台,是说到死亡不用眼泪,说到新生不用鲜花的理性和高妙。读她的小说,似在捡拾诗的珠贝,似在与一位诗人对话,因为她的语言里有穿透铁质的光速、有在翻动蓝色的火苗,也因为小说第一人称的存在,让读者与作者之间,有了更多盘腿而坐的机会。说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都在同时打捞关于一个部落的百年沧桑、多舛命运和风雨归途。
她的小说里,动物是行走的背脊,这背脊参透了驯鹿、狼和猎鹰迁徙的一生。而驯鹿承担了鄂温克族人几近百年的向导和告示。人与动物之间所传导的爱和珍视,早已超越时间本身,成为真善美的化身。而额尔古纳河右岸这广袤的草原,也在作者笔下毫无悬疑地成为驯鹿的至美天堂。人与自然与动物,在这本小说里创造了无限的可能:前赴后继的驯鹿,让鄂温克族人卸掉坚硬的铠甲,在一场漫长的迁徙中,采撷到善意的目光和友谊。这是此书所赐予的另外一种光亮,这光亮是生态的胜利,更是人心的胜利。
她的小说里,自然充满光辉:森林、树木、白云、流水、落叶、日月、清风、苔藓、蘑菇与石蕊等,每一处都有生命起舞的芬芳,每一处都深沉、静朗,让人情深而不知所往。在这些清丽的面貌背后,她笔下的一面伊莲娜用过的小镜子,不止照出了自然的情态,也照出了一张女人苦难的脸,这面小镜子它代替很多人的眼睛,把生命的苦楚、欢腾的草木得以悉心收藏、沉郁表达。小说中大规模的景物镜像描写,我自觉以为,它就是在借景物之光点亮现实,用光晕生发小说,让圆满的地方比对缺陷的部分,让残缺自愈,让背后的光芒显身。在她的小说里,所有的苦难都有透明的膜包裹,我不知道一个成熟的作家,她是用怎样的手艺和心思制造膜、运用膜、挑开膜并剥落膜;她是用怎样一种平淡而哀伤的口吻,讲出北方山林里几代人的欢喜和忧戚的。她笔下的鄂温克人,带给我们的是神秘的力量,即使在生死面前,故事里的人依然保持着明亮却从不刺眼的品质。在小说的阅读中,我承认我是一个控制不住情绪的人,我在一个民族生存的土壤和季候里反复挣扎和呼救,但解放我的却始终是平静的萨满信仰和萨满精神。
不过多地索取,在盈亏中自珍,在逆境中铺陈,在顺势里归拢,也许是更多现代人萃取的智慧之所在。读此,还有哪些静不下来的事物呢?春与秋隔着一起大火,也隔着一场大雪,事物注定在安静处待发,注定在动荡时萎缩,红尘一骑,起于尘也必绝于尘,于是知道,所有的生命,都需晾在时间里自由地蒸发和隐退,自由地欢喜和伤悲。读此,卸掉精神的内耗,跟随一条河,领受山川湖泊的教诲,领受日月星辰的照拂,在一本书里获得宁静且自愿沦陷,用一个辽阔的故事,分散灯祭背后的温暖和伤感,聚集手心空落的独寂和无常。读一本书,像度过住在别处的一生,这种体验就像闪电从高空滑过,而我们的脚步也即可踏离混沌一般。
很想在一本书面前起誓,去追风吧,去追光吧,去追逐热爱的一切!我要深刻知道,病理的生活,需要阳光的行动去手术、治愈和创造。也很想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水声里,寻找一种腔调、温度和勇气,因为它胜如我捧过的诗束,总在我迷惘之时,奉命在我必经的道崖和树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