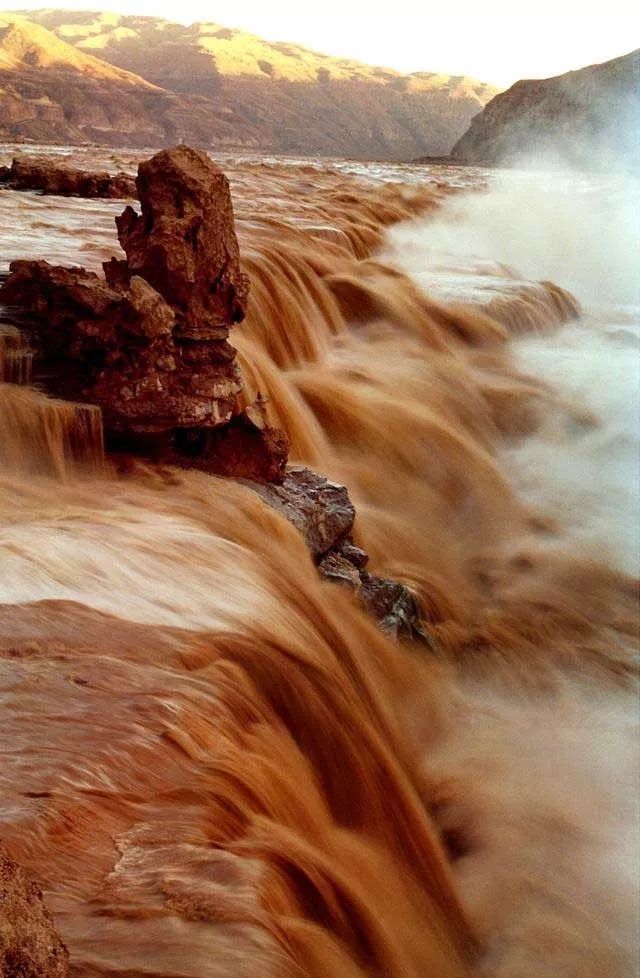文/李贵龙
乌云似汹涌的波浪,一浪一浪从天的西边涌来,雨一阵急一阵缓地下着,连绵昼夜下了五六天还没有停歇的意思。秋天的雨,落在地上激起一团团寒气,滴在身上就是一个个寒颤。淅沥沥的雨声敲打得人心烦意乱。

户家大哥踏着泥泞、冒雨又挑回一担南瓜,边往窗台上垒边闷声闷气地说:“谁把天捅开了个窟窿?雨下起来就没完!”落汤鸡似的看着怪遭罪的,我问:“为啥不等雨停了再往回摘?”“雨水里泡了五六天了,泡烂了怪可惜的!”
是啊,不起眼的南瓜里涵容了四季的辛劳、农人的期望,还有人寿年丰的祝福。面对连绵秋雨,成熟的南瓜,和雨中的摘瓜人,我想到了唐代诗人李绅和他那首简朴浅俗而又凝重沉厚的诗。
寒窑地下、窗台上,都是南瓜,长的圆的椭圆的,黄的红的桔红的,堆了一层又一层,似搭成的积木很是好看。看来,今年南瓜确实丰收了。
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多南瓜了。住在小城,菜市场里看到的南瓜,仅仅是南瓜,确实没有乡野的、荡魂摄魄的气场和视觉冲击力。农家里的南瓜,个个像有故事、活蹦乱跳的精灵,抚摸,有生命的温度;对视,可进行情感交流。
曾记得,父亲也爱种南瓜;好像是,村里的叔叔大爷都爱种南瓜。
那是早年的事了。当时我才十多岁,父亲就领着我,到离村不远的、叫做受苦梁的地里种南瓜,我的任务是点南瓜籽。瓜砵子是大地刚刚解冻父亲就挖好了的,二尺界方,一行一行地排列,株距行距十分匀称。上足了底肥,每个瓜砵正中用镢铆捣一个坑,待到“立起夏,安瓜种豆”时节,瓜籽入坑,覆土,轻轻镇压,南瓜就种好了。
南瓜种得太多了,正地里种了够半亩,还把所有高过人头的地畔上,父亲都掏好了瓜砵子。从早晨种到半前晌,还没种了一半,我就嘴噘得老长,蹲在地上不点了。其实,点南瓜籽的活不重。父亲只好领我坐在杏树荫下歇一会儿。
“南瓜是个好东西!”父亲猛吸了两口老旱烟,看似无心却有意地说,“它是最知受苦人饥饱的庄稼。现在入种,五六月就结成老碗大的南瓜。五六月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好多家户揭不开锅了,南瓜正好补了空缺,既当菜又当粮,让人们度过那饿肚子的苦夏!摘下的老南瓜,从冬能吃到春,又是度过春荒的好吃食。”父亲打着火镰,再点一锅烟,边抽边说,“多种些南瓜,熬点,但不用饿肚子。”
童年的记忆里,最怕的就是“饿肚子”。那滋味儿没有一丁点儿幸福感可言。为了不饿肚子,我强打精神,赶晌午帮父亲把南瓜全部种完。种下了南瓜,也种下了不饿肚子的梦想。
父亲营务南瓜十分上心,像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瓜地锄了一遍又一遍,吓得野草从春到秋都不敢露出脑袋;瓜苗举着两只绿茸茸的耳朵破土而出,就要间苗,培土;抽出瓜蔓,要在中午的骄阳下埋蔓覆土,这是埋蔓覆土最好的时间;追肥更是不可或缺的要紧农活,俗语叫“奶南瓜”,至少要奶两三次;南瓜的分蘖能力很强,每片叶腋处都会生出瓜蔓,称作“胡头子”,掐胡头子也是隔三岔五、从夏至秋进行不止的……营务南瓜确实是很费工夫的细致活。
在父亲的精心营务下,我家的南瓜园简直有了园艺的美感。远处一望,竖成排,横成行,株株南瓜平行而齐整,朝一个方向茂腾腾地生长;更像翠生生的荷塘,荷叶状的瓜叶在风的引导下翩翩起舞;嫩黄的瓜花娇艳欲滴,引来蝶飞蜂鸣;成熟季节,红的黄的绿的桔红色的南瓜,将瓜地点缀成一块五彩缤纷的织锦缎。
父亲的口头禅:“人勤地不懒。”父亲的心血汗水洒向瘠薄的土地,滋养出一个丰硕的金秋。南瓜堆满了寒窑、窗台、柜顶……堆出了满院子年丰人寿的喜悦,和农人简单而纯朴的幸福。
太阳从云层的缝隙间探出了笑脸,连绵的秋雨终于停了。我该去父亲种过南瓜的地里去看看。南瓜地的名字、位置、形状,和通往南瓜地的羊肠小路,至今清晰地储存在我的脑海中,父亲却离开瓜果飘香的世界已有四十多个年头了。
呈不规则三角形的南瓜地,位于村东的一道山梁上,是少见的平缓山地,黄土层疏松而厚实,四十多个年头过去了,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不同的是,地上长满了杂草,黄蒿、艾蒿、菅草、白茅、刺荆、苦菜……你争我抢拥挤出令人心痛的荒凉;那棵杏树也苍老得枝柯稀疏,叶片过早地染上了衰老的桔黄色。
又是南瓜收获时,徘徊在父亲的南瓜地上,南瓜的清香似乎还在杂草间飘荡,土壤中还能闻到父亲汗水的味道;恍若看到父亲头顶烈日营务南瓜的身影,还能看到我随瓜砵子踩下的竖排横行、稚嫩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