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毓海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篇章,党中央、毛主席运筹于山峁沟壑,决胜于千里之外,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防御历史性地转为战略进攻,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作为转战陕北的主要活动区域,榆林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留下了感人肺腑的历史佳话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为纪念这一伟大胜利,重温这段光荣历史,缅怀先辈光辉足迹,弘扬红色革命精神,2019年12月22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和中共党史教研部、军事科学院科研部、陕西省委组织部、中共榆林市委在榆林共同举办“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高端理论研讨会。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应邀与会并作了发言,本文为韩毓海教授在会上的发言摘编。

毛主席转战陕北(资料照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宽阔的历史视野,去认识伟大的中国革命。毛泽东主席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我们党是中华文明优秀遗产的继承者、发扬光大者。围绕这些精神,我谈几点体会。
首先,认识陕北、榆林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陕北和榆林,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源头。4300年前建立的石峁文化就在这里诞生,它的规模超过了陶寺、良渚遗址,从石峁遗址出土的石雕和石刻人像,高鼻深目,戴着异域风格的尖帽子,这显然不是一个中原文化的遗址。
陕北和榆林,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区与蒙古草原、山地区之间的交汇带,这也是我们后来所谓的“长城地带”。在这个地带诞生的文明,比中原地区的文明,更早地掌握了青铜和铁的冶炼技术。这里的民族是骑马的民族,他们与雅利安人在中亚地区的运动有密切的关系,这种事情发生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商代把这个地区的部落称为“鬼方”,商朝的灭亡与鬼方的东进有关,周代处于这个地区的则是赤狄和白狄,而西周的灭亡则与赤狄和白狄的东进有关。因此,我们必须从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来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来认识榆林和陕北在我们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来认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在陕北的活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毛泽东主席的雄才伟略,甚至才能真正读懂他的《沁园春·雪》。

第二,如何认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如何认识中国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问题。
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举世瞩目的长征时期,1935年,有一个名叫冀朝鼎的中国人在美国出版了一部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李约瑟曾经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这是一部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出发,阐释中国历史的杰作。特别是冀朝鼎提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重要范畴,指出在传统中国那样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建设,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的建设达成的,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只能看成是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中下游,三国、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同时也迅速发展,元明清三代,除了继承了上述基本经济区外,由于首都离基本经济区太远,遂有开发海河流域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中国的所谓国家能力,其实就是控制与建设上述基本经济区的能力。所谓“统一”与“分裂”的根源,大抵也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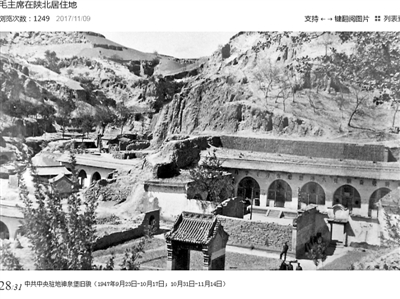
中共中央驻地神泉堡旧貌(资料照片)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差异,影响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土地制度、赋税与商业以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冀朝鼎的这部杰作,当然是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充分完善,其核心观点至今依旧难以超越,它深刻揭示出唐宋以来中国治理体系之要害,就在于长江流域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从这样的角度看去,从王安石到顾炎武,一切改革之要旨,皆在于增加官员(官僚体系)治理这一区域的能力。
但是,冀朝鼎的著作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于元代以降中国治理问题的重大变化注意不够。因为元代以降,中国的版图极大地扩大了,北方草原文明进入到中国的版图之中,元代的治理体系是从治理草原地区的经验发展而来,明代则进一步有了“海国”的问题,而到了清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终于包纳了居国—行国—海国三个方面。这样一来,元代以降,中国的治理问题,当然就不仅是增加对于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的问题,王安石以降那个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问题,则进一步成为魏源所谓:如何统合居国—行国—海国之间动态平衡之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的治理问题不仅是一个立足于基本经济区发展经济的问题,而更是一个维护包纳以上三种生产方式的治理体系的内部复杂平衡的问题。简而言之,维持这样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运行,与增加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我们说“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不是一回事的意思,若追本求源,大致而言就在于此。
简而言之,唐宋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增加国家的经济财政能力,其核心就是对于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称为“治理能力问题”;而另一个,则是维护三种生产方式之间的融合与平衡,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就需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中原与边疆之间的关系,《论十大关系》中集中讨论的问题,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治理体系”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在于治理能力下降所导致的经济、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实际上,清代的经济总量并不低),而在于治理体系瓦解造成的国家分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主席的那个洞见是完全正确的——控制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控制中国。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势,并非是以居国去统治“行国”和“海国”,甚至不是以南方去控制北方,恰恰相反,中国发展的大势是以边疆包围中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体系控制南方的经济区,毛泽东主席的视野超越孙中山、蒋介石,以及那些妄图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之处,庶几在此。
因此,冀朝鼎的论断,固然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要害,但却不能回答和面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帝国主义要控制的,恰恰也是上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且是从海洋方向进行控制,反过来说,就是清王朝控制海国的失败,导致了与海国密切联系的基本经济区治理的失败。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上述基本经济区的瓦解,导致了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和中央集权的崩溃,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政权,都不能不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欲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政权,要么必须与帝国主义结盟,要么必须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盟,这就只能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除此之外,便没有出路。
那么,在基本经济区被从海洋方向控制的条件下,中国重新恢复国家能力的立足点,究竟何在呢?冀朝鼎和那个时代杰出的学者当然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孙中山、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更没有这样的视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主席。
第三,通过大历史的视野,谈谈毛泽东思想,谈谈中国共产党的长征和毛主席的转战陕北。
与蒋介石及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不同,毛泽东主席所瞩目的不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是这个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地带”,以及基本经济区内部的“边缘人口”。
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短视的近代革命者不同,毛泽东主席关注的是行国—居国—海国之间的动态的平衡与不平衡。与此相关的,便是核心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
毛泽东主席的革命理论,当然与苏联的无产阶级城市暴动学说同样有很大的差异,实际上,他的思想起点,是通过突破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简而言之,毛泽东主席的革命不仅是一场阶级革命,更是一场文明革命、文明复兴,是为了恢复晚清之后瓦解了的中华文明的内在平衡而进行的革命。在毛泽东主席看来,正是因为这种平衡的瓦解,中国的传统治理体系解体了。
毛泽东主席很早认识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一种开放的动态平衡体系,作为“居国”和定居的农耕区,其人口历来是流动的,其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是空前的,而最大的外来人口是被称为“客家”的族群。“客家”是魏晋以来,在草原文明的挤压下,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一个持续性的结果,江西和福建是中国客家的重要落脚点。由于当地的土著人占据了平原和平地,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山区,不得不在逼仄的山地求生。中国基本经济区的土地问题,在土客矛盾中得以集中和放大。
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湘赣边界井冈山的斗争,当然是农民的土地革命,但更为确切地说,这也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客家人的支持,“井冈山的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一时期,红军和党内出现的各种分歧,即使可以被视为路线斗争和路线分歧,但是,如果不考虑当时的党内、红军内部存在的土客问题和土客矛盾,这种分歧和斗争就不能得以深刻地解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一种真切的、血肉交融的结合。毛泽东主席不但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基本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而且,他更为深刻地洞察了中国存在的三种生产方式的不平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随后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基本上就是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基本经济区与草原山地文明之间的结合部进行的,而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客家人的聚居区——赣南和闽西出发,穿越苗族、藏族地区,直达蒙古边界的回族聚居的陕甘宁。
什么叫“地球上的红飘带”?当建立在三种生产方式内在平衡基础上的中华文明,在近代走向瓦解的时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奇观,重新把草原山地文明与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联系起来。如果借用魏源的话来说,这就是以革命战士的血肉之躯,把“居国”与“行国”重新凝聚为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纵横两万五千里,牺牲惨重,而正是这种惨重的牺牲,完成了破碎了的中华文明的重建。当毛泽东主席把长征称为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时,我们应该深思:怎样把长征视为中华文明内部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正是这场革命,导致了中华文明的重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长征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写照。
有了这样的视野,我们就可以再来看转战陕北的意义。我坚信:我们的后人终将有一天会这样理解转战陕北的伟大历史意义。因为更为发人深思的是:1948年,当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泽东主席再次率领中国共产党人转战陕北——他亲自带领的部队只有不到800人,他们先是一路北行,几乎抵达内蒙古核心区的毛乌素沙漠,然后在陕北的佳县、吴堡东渡黄河,沿着山西一路疾行,最终到达位于河北、内蒙古和东北交界处的西柏坡——这条道路,划出的正是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分界线。
转战陕北,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行国”——即蒙古战争方式,是草原战争方式对中原战争方式的胜利,它是以没有后方、断掉后勤,高度机动的突击方式,击溃了高度依赖后勤辎重,高度依赖官僚程序,因此移动缓慢的敌人。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以骑马或徒步的革命,把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重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这个结合带的革命化,特别是“长城地带”的革命化——它是长征造就的“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延续与完成。
在这条道路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主席,同时走在了秦皇汉武、成吉思汗的道路上,他以徒步行军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华文明结合起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国道路。
中国革命当然是一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但是,如果把波澜壮阔的长征与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联系起来看,那么,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就是一场中华文明史的浓缩版。因为从漫长的历史看,中华文明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草原山地文明包围基本经济区、占领基本经济区,并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治理体系的过程,是中华文明在这两大区域的融合中,不断走向复兴的过程。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著有《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龙兴:五千年的长征》等。)

